ISBN: 9780415026710
提出的议题本身确实有价值,可如果文艺作品只是观点宣言,没有论证过程,到最后,是否也只会沦为在当今众多回声壁里的一道回声?
最近比较闲,春节回了老家,过上一种晚上看曼德拉记录被吓得半夜不敢去上厕所缩在被窝里撸表姐的猫,白天吃完舅舅手搓的鱼肉牛肉鸡肉鸭肉火锅就背着手去姥姥的菜园子里面蹲着看家里种的白菜菠菜香菜萝卜的惬意生活。乡下农村没电影院,春节档大热电影一个热闹没凑上,现场演出当然也是很久没看了。春节结束后努力过健康生活,尽量减少去商场的次数免得自己看到饭店馋,结果这健康生活真的过不下去一点,每天半夜狂吃麦当劳。
在这样的日子里,刷毛象和微博的时候都有看到了《初步举证》的推荐,体感口碑还算不错,于是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一上午搜索附近的电影票,在下班后跑去看了。结果坐进电影院椅子,屏幕亮起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部话剧官摄,并不是一部电影。
接下来我会谈到一些对这部戏的感想和沿伸,虽然我个人会觉得这种观点鲜明的戏没啥剧透预警的必要,但是如果有人在意这个可以到这为止不要往下看了,后面我在讨论的时候会有很多剧透的内容,嗯嗯。
作品本身
内容梗概
女主角泰莎是个精明能干的刑辩律师,是法庭上的常胜将军,通过个人奋斗甚至实现了阶级跨越,获得了本地顶级律所的青睐,收到了工作邀请。她在一次胜诉后和律所里富有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男同事眉来眼去,暧昧来往。在她和男同事的一次约会后,她邀请男同事回家,两人喝酒,然后做爱。女主角因为喝了太多酒,比较难受,半夜起来扶着马桶吐,吵醒了男同事。男同事握着她的手等她吐完抱着她回到床上,想要和她做爱,她因为难受不愿意做,男同事按着她的手捂住她的嘴强奸了她。被强奸后的女主崩溃地哭了很久,疯狂洗澡,然后出了门决定报警。
警察给她做了笔录,让她去医院验伤取证,之后让她等消息,因为是否立案取决于皇家检查院(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决定,最后问她是否愿意出庭作证,女主角说愿意。被强奸后的女主角回到公司,男同事还试图和她调情,女主无法忍受,跳槽去了之前给自己伸出橄榄枝的大律所。后来警方下了逮捕令,把男方逮捕了,女主立案成功。
下半场以报警的 782 天后,女主角进入自己案子最后一次庭审的心理活动开场。她是这个公诉案件的第一个证人。进场后,女主角意识到辩护律师都是男性,法官是男的,坐在 bar 里的人都是男的,陪审团有四名女性(妈妈紧张地问:是好事吗?女主说不知道,有时候女的也不愿意相信别的女人。)女主先做了自我介绍和过程陈述,描述了自己说了不,被人按住双手(无法直接反抗)捂住嘴(无法尖叫出声)被强奸的过程。
随后进入 cross-examine(交叉质询?搜索直接翻译叫盘问,我理解是一方律师询问另一方证人所以叫交叉)的环节。对方的辩护律师的辩护有三点:
- 想要通过故意挑起女主角的创伤的方式模糊女主角的记忆,之后恶意提问:女主如果双手被对方双手按住,对方是没有第三只手来捂她嘴的,所以她的嘴是她为了回避让口臭熏到男同事自己捂上的,她是有反抗能力的,只需要拿开手,而没拿开证明了女主是愿意的,是给了 consent 的,不是被强奸。女主角在混乱后想起了细节,男同事用一只手按住了女主角两只手,另一只手捂住了嘴,所以这个理由不成立。
- 暗示两个人都在竞争同一个职位,女主角报案是为了消灭竞争者。这个问题以问女主是否喜欢新工作更大的办公室开头,被女主以自己出身底层,很知足,不太在意办公室到底多大回绝。之后的诛心之言,女主角回以“你觉得女性会为了这种事情耗上这么多吗?”并痛陈自己失去了尊严,安全感,心理健康,对性的享受,“但最重要的是,我对法律的信仰”。
- 暗示女主是因为知道男方把两人搞暧昧在办公室里做爱当作风流韵事与朋友分享,自己的隐私被传播后恼羞成怒报复男主才这样报案。女主觉得不可思议,自己案发前几天还和同事说自己似乎要爱上男方了,根本不知道男方还做过这样的事。
泰莎被对方的询问激怒,突然冥冥之中顿悟(噫!好!我悟了!)并说个不停。对方的律师反复抗议,因为女主角讲的话与他的讯问内容无关,是有偏见的在动摇陪审团的内容,申请 voir dire (预先审查?),法官同意,于是陪审团离席。女主角对法官发表长篇演讲,以“我也曾经以‘证据(证言?英文是 evidence)可以被以简洁、有逻辑的方式组织并呈现’为前提,质询过证人,但我现在意识到这个假设是不对的”开头展开了论述。要点有:
- 因为被强奸是会让人产生创伤的经历,会导致受害者的记忆不是那么整齐、连贯、科学的,而这样的证言会让法律认为受害者的证言不可信;
- 法律会让受害者觉得,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经历以正确的线性方式陈述出来,那她们就在撒谎;她理解法律不能抛弃对连贯性的要求,但是性侵案里这个标准是否能用于评判证人的证言是否可信?
- 在一段关于性侵对女性造成影响的陈述后,提出:“性侵相关的法律围绕着错误的假设展开。一名女性被性侵的经历不会符合男性定义下的系统对真相的要求,所以不会被认为是真相,也因此无法获得正义。法律系统是由一代代男性塑造的……我们不拷问法律但拷问受害者……”
- 最后总结陈词,“法律是有机整体,它由我们定义,由我们的共通经历铸造,它必须被改变”,只有倾听女性声音,法律才能主持正义。
法官说她的演讲超出了她作为证人被允许陈述的范畴,voir dire 结束,陪审团回来继续走流程。女主环顾四周,最后结果下来,陪审团认为男方无罪,女主角站在舞台中央说,“我知道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一些事情必须发生改变”,之后落幕。
个人感受
表演本身没什么问题,情绪的调动和台词节奏乃至身体状态的呈现都很有力,作为一个看话剧并不算特别多的一般通过观众,这个戏让我觉得演员确实把文本给的所有点都打到了,非常出色的演出。舞台设置也很好,小舞台,最后的那一本又一本案件书……我愿意给 9/10 的程度。
文本嘛……
7 /10 吧。故事文本逻辑不成立,4 分,煽情煽得好加 1 分,小节奏做得好,加 1 分,独角戏文本有固有难度,它大体做到了完整,加 1 分。整体上,我还是推荐的,我认为市场上这样的戏多一点也没关系,推荐给满足于情绪共鸣、对女性议题有关心并且大体上价值观比较进步的观众。但我个人对它的文本意见很大,所以我不推荐那些本身价值观已经很激进并且对文的本要求相对高的观众。
当然,作为一个中国大陆音乐剧市场的受害者,我有时候觉得,呃,就我看过的那些现场演出的文本水平,我可能也没什么资格点评这部剧的文本,毕竟那样我都忍了。但怎么说呢,话剧毕竟没有演唱和音乐,那我多拷问一下文本也没什么吧?
我出电影院后努力这样向朋友描述这部戏剧:观点进步的……那个公众号爆款文章女王叫什么来着……咪蒙,对,咪蒙。
等等,我可以解释。
这个戏文本上是有优点的,很多小节奏很错落,各种舒缓和张紧的部分都很好。独角戏怎么处理叙事和对话的描述也都蛮精确。我对这个戏最大的意见是,过程很重要,可惜它没有。如果把这部戏看成一篇议论文,它有论点,有论据,但是没有论证过程。
从结构上看,最重要的显然是结尾的时候,陪审团退席,女主角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对大法官发表的演讲。演讲要点概括一下,性侵的受害者作为受害者,有时候无法给出一个逻辑流畅前后一致的证词。在多重创伤下,受害者给不出完美证词,这不是受害者的错,而当下的系统有问题,很难考虑到这一点,因此系统需要改变。
OK,很好,没问题,结论我完全赞同,举双手双脚。
问题是它之前的文本完全没有证明这一点。虽然她的台词里有类似“我一遍又一遍交叉质询自己并感到 defeated”这样的概括性陈述,但是戏剧里面没有任何部分直接写她怎么交叉质询自己,怎么给自己准备答案又失败,怎么发现自己的经历和答案无法组成一个前后一致、逻辑连贯的证词,怎么和律师沟通,怎么梳理自己的经历,这个东西又怎么不被法律采信。
单看女主角的案子。
- 她的证词,逻辑上有不连续或者前后矛盾的地方吗?客观来看,是没有的。对方律师虽然试图挑拨她的情绪,但她自己给出的证词,如果忽略她情感上的动荡,单看逻辑,并非是不连贯不科学的,对方律师试图抓住她的漏洞,但她想起来了,她破解了,她破局了。事实 prevail 了。
- 法律会让受害者觉得如果自己证词不够标准那就是自己在说谎,女主前后有任何一刻觉得自己在构陷在说谎吗?没有。
- 法律有因为她的证词“不连贯不科学”而不采信吗?文本上这部戏里没有任何她的证据和证言,因为不够可信被系统禁止呈堂的内容,法官一开始还允许她稍微溢出提问范围的回复,只有她开始大演讲的时候,法官才让陪审团退席。
造成她没有获得正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方的辩护律师辩护的三点,其实都是围绕着让她在陪审团面前显得不可信来的。先是试图说她有给性同意,之后是说她构陷男方,居心叵测。但是陪审团不愿意相信她在这个文本里不是系统的问题;陪审团是从社会上随机抓来的人,反映的是社会共识和民意(如果外国像中国一样,是法官直接下判决,倒可以说是系统的问题了。)此外,对方辩护律师构陷她也不是系统的问题,辩护律师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执法机关,并不代表系统。
我觉得这是这部戏最没能说服我的一个地方。它设置女主角的身份是法律从业者,显然就是想要落“即使是熟悉规则甚至能够驾驭规则为己所用的世界之王,当变成受害者,成为被系统拷问的一方时,也会意识到系统的不足”这个点。但问题是中间的这个过程它很少描述司法体系直接对她有不公,只有泰莎站在证人席上和对面律师交锋的时候的溃败和羞辱,体现了一部分这样的表意。——但是,这种溃败和羞辱,也并非是系统直接加诸在她身上的。
泰莎直接面对系统的唯一一句台词,大意是这样:“为什么我作为受害者,我的真相需要我站在证人席上滚钉板来自证,凭什么他作为加害者却不用?”这是我认同的,属于系统的问题的部分;也应该让加害人上证人席,接受我方律师的拷问,在群众面前有被当成骗子的机会,这是我唯一看到的系统性的不公,但是似乎在大演讲中,没有重点指意这一事实。“我们不拷问法律却拷问受害者”,呃,我觉得你文本里说的似乎是:“我们不拷问施害人却拷问受害者”?
作为一个法律的外行人,我会觉得最后的演讲,纯从文本的角度出发,抛弃我的固有立场和对现实的认知,这个联系实在有些牵强。泰莎没有得到正义,这是陪审团做出的决定。在这部戏里,如果她想要得到系统审判的正义,她应该做的是想办法移风易俗,改变民心,让陪审团对受害者证人的证词更加有同情心,而且愿意采用和相信她的言论。对方律师的言论对她造成的羞辱,也恰恰是社会舆论角度的构陷,并非是直接法律事实上的证据不成立或者不稳固——那这就不是系统直接带来的后果。(当然,系统对民心有引导作用,但文本里没有,我不引申。)
但是,她最后的演讲,也并不是直接面向代表了社会民意的陪审团的演讲,而恰恰是在陪审团离席后,直接对大法官发出的,是一种屏蔽了对群众的影响后,作为系统内的一个人,对着系统内的另一个人,发起的一场内部讨论。是“我们”法律系统做的不够,所以“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
不是说最后这个结论不对,而是——就比如说,取证的流程里面有写她马上后悔,因为被性侵完洗澡了,把证据洗掉了,或者之前还被人看到和性侵她的人有说有笑;她担心这些会不会都被当成让她显得像个说谎者的证据?但是到了真正的法庭审判的戏里,这种她可以被对方的辩护律师拿出来说她当时是同意的因为她之前一直同意,的辩护理由,都被——或许是出于叙事效率或者戏剧效果之类的理由——省略了。
后面突然的“男性铸造的法律系统无法让女受害者的真相符合标准”更是空穴来风。这个戏一直在塑造一个二元的对立,辩护律师是男的,强奸犯是男的,法官是男的,警察是男的,想给我支持的法警是女的,温柔的法医是女的,妈妈是女的,好朋友是女的。但是男女二元是这个系统问题的根源吗?假设对方辩护律师换成一个和以前的她一样的女生,那她会获得她想要的正义吗?如果陪审团换成十二个女生,那她会获得她想要的正义吗?更何况,男性的强奸受害者,难道因为是男的,就能给出前后一致逻辑连贯的证词了?我理解这部戏想要踩女性主义市场的点,但是女性主义市场从来不是性别本质论的呀?
下半场我看的时候一直在哭。这部戏在情绪上引发的 cartharsis,我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题材上,确实没法做到漠然。女演员充分演出了情绪的强度和高度,某些时刻我甚至觉得完全可以和剧中的人物感同身受——可是即使这样,她到最后不还是形成了一个说得通的前后一致的证词了吗?看到大演讲我特别愕然。我觉得,虽然我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让我也认同“系统有问题”,但是,在你这个案子里,你这笔账难道不应该算陪审团头上?个案的正义和系统性正义虽然外在表征相似,但是方向是不一样的(朋友箱子语)。
根据前面的文本,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落脚点是“法律的真相未必是事实的真相”,一部分因为是前面的台词有提及,另一部分是因为上半场她在同意 - 不同意之间的变换十分细微,在逻辑上的前后不一致,会让法律上不承认她的真相(和朋友塔塔聊的时候她提出了这个亮点,我也觉得是这部戏做的很精巧的地方),但是它最后的演讲是“系统是男的造的不够理解女受害人,所以大家都要多听多信女的”,我真的:啊?怎么飞来一个彗星?错愕,不解,不得劲。
所以虽然我看这个戏一直哭,但是我不是一个自己一哭就会被说服的人,我不需要通过 validate 作品来 validate 自己被作品引发的情绪,我的情绪本身就很宝贵——借用 Nicki Minaj 的一句歌词,“I’m not difficult, I’m just ‘bout my business.”
综合感想,情绪上一泻千里很厉害,但是很多东西经不起仔细琢磨。这部戏本身提供的材料无法完全说服我,它依赖抒情的表演,依靠调动观众的情绪,需要建立在目标受众已经对性同意有共识对现实社会的法律有共识结论的基础上,才能使其立论成立。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给我感觉,呃,咪蒙,的地方。有些文艺作品喜欢放“金句”,放一些能够和观众共鸣的观点,以此拉进观众和人物的距离。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金句”就是你的全部,共鸣就是你的全部,观点宣言就是你的全部,那么,你身为一部作品,到最后,是否也只是面向特定群体的一场集体自嗨?
(同样也是我不喜欢看一些虚构作品的现实考据的原因,如果一个东西单看文本不成立,要靠现实来贴膜,那我们应当承认贴膜也只是贴膜,无论是什么方向的贴膜。)
戏外的世界
当然,前面的评价只针对作品本身,并没有考虑到作品立论的现实考量。或者说,“文艺”的部分结束了,“法律”和“政治”的部分还有待考量。
现实的法律
这个戏看完以后我总觉得难受,盘了几天没想明白,后来有一天和当过律师的朋友箱子聊了这部剧的一些内容和细节,她作为专业人士给到的信息和看法让我更加理解了这部戏,所以为了补全我也贴在这里。
戏里的法律环境
#1 被告可以不出庭吗?
箱子说,法律上,只要能证明二人当晚发生过性关系,那么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就会变成到底有没有性同意。(台词上,泰莎刚被强奸完洗完了去报案的时候点过,担心万一男同事不承认二人有关系怎么办,但是马上说他不可能那么蠢。)但是当讨论焦点变成到底有没有性同意的时候,这个案子就变成了一个 he said she said 各执一词的情况,这时候双方都是必须被揪出来交叉质询的,不太可能出现受害人作为证人被质询,但加害者可以坐下面优哉游哉的情况。
她还讨论,这部戏的表达也是想要参与到 me too 运动里的一部分,因此它可能想要在这里影射一个现实里 me too 运动里程碑的案件——韦恩斯坦案——因为韦恩斯坦案里的男性也没有出席。但是,法律现实上,他可以不出庭的原因是他涉及的案子里的性侵事件是一些倒追十年甚至更久以前的案子,所以想找存在性关系的物证本身就很困难。这个案子里,虽然泰莎在被强奸后洗了澡,但是强奸案里精液不是唯一的证据,阴道的撕裂伤,床单上的精斑,家里的指纹,这些都也可以是证据,事情只要发生过,就不可能是孤证,更何况她是在被强奸的当天就去报案的。
所以这个案子本身为了戏剧冲突和表意,虚构了一个现实中本来就不太可能存在的情况。
#2 系统对泰莎不公平吗?
按照司法逻辑,这个系统对泰莎的态度还算 OK 的。警察虽然开了一记小嘲讽“现在你需要我们了”,但仍然记录了她的报案,让她验伤,替她收集了证据,把案子立起来了,还对男方下了逮捕令,让她的案子走一个公诉的流程,是刑事案件(所以台词里是女王对男同事(真想不起伊的名字了,不重要)案,不是两个人互相诉讼的案件。
此外,她的案子也通过了预审,立了下来,可以走后续司法流程抬到陪审团面前,并没有说法律系统里的人因为觉得她的证据不可信就不让她立案(虽然台词里她有提到皇家检查署觉得两个刑辩律师打官司很有趣,但没有直接说这个才是立案成功的原因)。
我:我是来看戏的,如果你理论是“系统不公”,我就要看系统怎么不公,结果我看下来没觉得系统不公,但是你甩了我一个“因为我是从业者,我说有就是有”,我觉得你蒙我?!!!就特别不爽。所以很纠结,但又觉得可能是我本身不够专业没看到法律上的问题,所以来问的。现在看来我的感受大体上没问题诶?
不过,陪审团一般有十二个人,箱子会认为四位女性的比例有点低——强奸案的陪审团遴选是很大的问题,很多男性天然会认为女性在说谎,在多元化案件中多元化陪审团一直是努力的方向。这里确实会有影响——但是,多元化陪审团很多时候也不仅仅是性别比例,也要看人种,职业,教育背景,等等等等。
#3 泰莎的不公平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
如果按照现实的法律流程,在她被质询后,男方也会接受质询。所以最后的大演讲,台词之所以不说“我们不拷问施害人却拷问受害者”,是因为现实流程里,这种情况,施害人也会被拷问。所以这句台词如果这么写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那么,如果忽略外部的影响,文本上,泰莎的“制度错了”,只能被解释为,“因为法律需要前后一致逻辑清晰的证词,所以允许对方男律师交叉质询的时候用这种方式讯问我,对我造成了伤害,所以这是系统的问题,系统不应该给他这个权力。”
但是这个律师交叉讯问的内容只有第一点涉及到了前后一致的证词,而且女主角给的证词确实逻辑连贯。后两个辩护点的台词有在扣一个“因为男的特别重视俗世的成绩和为了龃龉无下限的报复,所以会想到用这样的思路来构陷我,从而进行辩护。”问题是,我会觉得,①女律师也有可能选择这样的辩护思路,因为这种辩护思路是社会(陪审团)可能会认可的思路;②男律师的辩护思路选择是否真的是在代表系统?
退一万步讲,就算女主的想法有道理,我这个外行人会觉得,yes, and? 你是觉得法律不该让任何性侵案的受害者被交叉质询吗?还是性侵的被告不可以有辩护律师?还是性侵案里的交叉质询里,某些在别的案件里被允许的提问方式在这里不该被允许(感觉涉及到法官的裁量权之类的问题)?还是说应当全部门成立一个伦理委员会来保证不让性侵受害者在被交叉质询的时候引发创伤?
箱子讲她对文本内容的感受是,是陪审团制度错了。因为对方的辩护律师会选择这么辩,会让她受伤和难受,用操纵、构陷和中伤,来让她显得不可信,是因为最终做决定的是 陪审团 。如果是法官在做决定,那么“没能获得正义”的结果大可以算到系统头上,因为法官根据法律判案,代表的是系统,辩护的争议焦点也只会围绕法律问题,也就是现有框架展开,更指向这个体系;但是对方的辩护思路完全围绕着取信于陪审团,因此最终还是陪审团制度造成了泰莎在这个情境里的受伤。
为什么叫“初步举证”?
讨论了很多,我还是很迷茫。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明白为什么这个戏要叫初步举证,女主也没举证啊?
箱子说她一听这个标题和主题就大概知这部剧的理念基础是哪本书:Smart, Carol (1989) Feminism and the Power of the Law. London, U.K.: Routledge. (OL)。一谷歌我就搜到了 pdf,链接摆在这里: https://ndl.ethernet.edu.et/bitstream/123456789/19696/1/7.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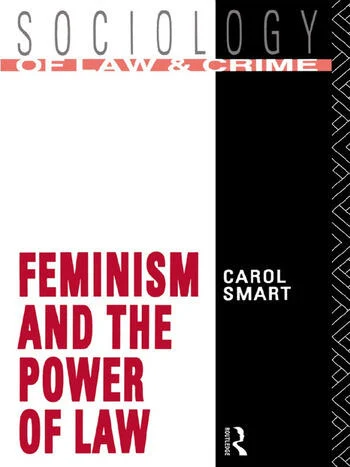
ISBN: 9780415026710
她对最后的大演讲的看法是,这个演讲其实没有回应司法一些流程里客观的对性侵害受害者的问题。或者说,这部戏其实就没有讲司法流程系统对性侵受害者的不公。
性侵犯的受害者在司法流程里受到的不公,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人“因为受强奸,所以没法给出符合男性主导的系统对真相要求的标准的证词”,主要是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这个议题在性骚扰案件里谈的会更多,虽然 me too 运动上会把性骚扰和性侵害一起谈,这两种案件在司法里面临的困境有时候会不太一样。正如前面说的,性侵害案件如果能够证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那能立案的话接下来主要争辩的其实是“是否同意”,而性骚扰要证明“事情发生过”会困难,所以会在举证立案上面临系统带来的不公。
很多法律学界的人都谈过,性骚扰案件的举证责任要倒置:因为“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举证责任太重,被告没有举证责任。
所以,这部戏如果延伸上面的逻辑,按照反映司法流程上的问题和“系统有问题”的主题去执行,这个戏的剧情会是,女主因为洗了澡没有了精液的直接证据,而其他部分的证据不被司法系统承认,女主角“初步举证”的责任没有尽到,无法说服法官两人发生了性行为,所以这个案子在预审庭(没有陪审团,只有法官做决定)无法立案,这是系统的问题。也有可能因为法官觉得两个律师打官司有意思,在她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允许她出庭,而她需要接受交叉质询是因为没有确切证据,所以额外需要通过证言补足自己的举证责任,从而受到伤害。而女主角承受伤害是为了补足举证责任。
我:哇,如果这样做我确实会觉得是系统不公,不会觉得她偏题。
但是,首先,台词里虽然提到了皇家检查署觉得两个律师打官司有意思,但这句话主要被用来刻画“环境冷漠无情,大家都在看好戏”,并没有说这是她能立案的直接原因。此外,对方辩护律师也没选择攻击她的证据不足,主要选择了污蔑和构陷,根本就没有质疑她的举证。整部戏基本没提到“举证责任”这个概念。而因为举证不足在立案上遭遇到的困难,而这个才是司法系统在性犯罪相关案件上真正的不公。
不过,转念一想……原来这才是为什么这个戏叫“初步举证”啊。我好迷茫,你说这个编剧不了解法律系统的问题吧,她又把这个戏的名字取名叫“初步举证”,你说她了解吧,她一整个戏批判的核心根本就没有围绕举证责任,全在讲“社会不够相信女的”。
箱子也提出了男性不用接受交叉质询可能是想要寓意,因为强奸案的原告举证责任太重,女性必须额外做许多事情,包括报警啊接受法医验伤啊出庭接受质询啊来补足举证责任,完成“初步举证”,但是男性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可能性。
我:当然是可以这么阐释啦但是阐释只是阐释,但是除了标题,戏文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去点“举证责任”的主题,所以我不太接受这种阐释。
荡开我个人联想的一笔,如果因为没有精液证据无法立案,也可以扣一个另一个系统不公,因为证据不是孤证,如果只承认精液是性行为发生的有效证据,那更可以扣因为现行法律就是一个阳具中心主义的烂货,所以“由一代代男性铸造的法律有问题”。(当然,阳具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不等于男的,但这么做我会觉得比大演讲逻辑更通顺。)
在欧美环境里的现实意义
箱子觉得这个戏到底其实是一个欧美社会运动技巧大全,一套很成熟的方法:先给你看个案不公,打动你,调动你的情绪,之后教化你法律有问题,最后落脚在劝诫观众去积极参与自己可以改变的部分。
虽然文本里,代表了社会意见的陪审团在大演讲的时候退场了,但是这个大演讲是直接对着观众席上真的可能去做陪审团的观众布道的,所以这个戏的大演讲讲着讲着最后一拐弯就到了“要多相信女性多倾听女性声音”——这么做的作品在欧美法律体系下是有现实意义的。如果去做陪审团的人愿意多多相信女性,即使法律系统的问题没有被改善,个案上性侵案件得到正义的可能性就提高了。
也因此,虽然文本在我看来是陪审团(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和共识)有问题,但戏本身会不指着观众的鼻子骂。这部戏从头到尾文本的目的都是移风易俗,大演讲正是它的核心。它的思路是,去尽量团结每一个能被打动的人,通过把账算在一个很虚的“男性铸造的法律体系”的头上,不去主动指责和讨伐其他人,从而让受众反感它的 message。而它之所以煽情,是因为在欧美煽情有用。可能大家哭了流泪了第二天就去做陪审团或者上街了,社会运动可以就这么简单。
如果最后结论指向陪审团有问题,民众会觉得“你什么意思,你指责我不够进步”;但如果围绕“法律系统有问题”的思路展开,结论落到法律系统是男性铸造的,我们要“多多相信和倾听女性声音”,那么欧美民主在法律参与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在对抗法律、对抗国家、对抗系统的自觉,这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主导的环境下是很有吸引力的,大家就会记得下次不要被辩护律师这些“坏人”骗了。
——当然,个案正义不等同于系统正义,民众参与去做陪审团,出对受害者更好的判决结果,其实并没有改变法律系统本身,也不解决举证责任的问题。但是结果能好一点也是好的,文本的取舍是有许多现实的市场考量在里面的。因此这个戏虽然文本有问题,但是放到欧美的话,它承载的现实意义让人更可以包容它的文本缺陷。
但是因为国内的司法环境与欧美不同,这个戏文化上离我们太远,教化现实的作用会很稀薄;也因此会让我觉得自嗨和咪蒙,因为这部戏文本不扎实不太说服人,所以它对现实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只剩下了“多多倾听女性声音”的回声壁,认为强奸都是女方活该的人根本不会受影响。所以这部戏引进进来,放到国内环境里,我就只能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艺术作品来看待,文本上的问题也因此在我眼里就更难以包容。
这是一部政治讯息很强的作品,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被创作出来就有社会意义在,文本扎实根本不是它的要求,市场导向用情感说服人是它选择的手段。但它确实有偷懒——性别二元的部分完全可以做女性法官女性辩护律师,最后说,虽然我们都是女性,但是我们在父权制和阴茎中心主义的制度下也不得不刀剑相向,从而剑指系统有问题。这是额外的话了。
政治,政治
说人话:贴膜 借题发挥开始了!
其实如果我们单纯看立意,这部戏当然有可取之处。相信受害者,认识到系统有问题,理解系统很难给受害者以正义,这些议题都是很好很好的,值得推广的,有进步价值的。我也觉得这部戏多推广对现实没坏处,但剥除文本本身的评价,我对它的政治 message 上是有一些异议的。
男性,女性?
她最后的立论里,突然提到,“法律需要前后逻辑连贯的证词……因为法律是男性铸造的,男性不理解女性奋斗的方式,所以需要改变”,我会觉得是相当,怎么说呢……
- 这句的潜在逻辑其实是,“因为男性更加理性更加讲究逻辑精密、前后一致,无法共情受害者,所以才会铸造出要求证词必须也无懈可击的法律”……这样带着性别刻板印象的潜台词,实在是很难让我认同。
- 我认为它这句话有一种,女性需要掌握权力,来到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参与到立法流程里,才能修改法律;这是一种与 girlboss feminism 同源的逻辑,并不提倡对权力系统的改革,而是提倡在现有系统下把男性直接替换成女性;因此这个句子出现在“系统有问题”的大段论述里会让我觉得特别扎眼睛;我对这种主张态度较为批判,之后有机会详细再述。
箱子会讲那句台词如果指意是想剑指父权制和阴茎中心主义的话,会有点学艺不精。因为男的不等于父权制。父权制是制度,制度的意思是换个人上去影响可能没那么大,男性,女性,不重要,毕竟女性里还有保守主义者呢。(黑人里还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呢!)
公平等于正义吗?
在下半场,泰莎的台词有“我作为受害者反而受惩罚,但他作为加害者不需要。”显然,台词认为泰莎如果获得了正义,那是加害者也受到法律制裁和审判,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失去自由。在上半场台词里,泰莎做刑辩律师的时候也会有提到,她会质问对方的证据是否充足,因为代价是她的客户失去人身自由进监狱。
我理解这种心态。我被无缘无故伤害了,我需要法律也让他受到伤害,来惩罚他。这样是公平的。
但是这就是正义吗?
之前在微博看到箱子讨论惩罚性正义与修复性正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般的现行法律的思路是,人们生活在社会中需要遵守既定规则,如果你违反了大家约定的共同规则,你就会受惩罚,让犯人受苦是法律的目的。这种法律的问题是它很多时候并不要求犯人明白自己的错误,犯人出狱后还有很大可能再犯(一方面,犯人可能不理解自己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只觉得自己是违反规则被抓到了,下次小心就好;另一方面,犯人在出狱后没法融入社会生活,只能选择进行非法活动,恶性循环)——甚至有的地方的司法和监狱系统鼓励犯人再犯,好让这些人重新进入监狱来为监狱提供廉价劳动力。
修复性正义根据联合国文件,大概是这个导向:修复性正义的根基是,犯罪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也伤害了受害者和社区。它主张在自愿的前提下,施害人与受害者、社区成员在安全环境下进行沟通和交流,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和“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达成共识,强调罪犯理解自己造成的伤害,产生悔恨,认识到自己需要为自己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并为修复伤害做出努力;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个行为有助于他们的创伤修复,对于施害人来说帮助他们重回社会并停止再犯。1
我个人看到的修复性正义有司法实践的案例是,组织性侵犯与被害人沟通对话,性侵犯因此意识到了自己对人造成了什么样的直接伤害,在出狱后持续积极参与咨询,受害者也因为经历不被否定和更加理解性侵犯的动机,对自己身上遭遇了什么的认知更加清醒,并感到疗愈的案例。
箱子其实不太认同“组织施害者和受害者沟通对话”。这也是一种方式,在加拿大也确实有人用,也有人说确实有效果,但她自己就是完全不同意。我对这种做法保持中立态度,因为我觉得让施害者意识到自己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并不是受害者的义务,更何况受害者还可能在流程里再次受伤——但是联合国文件强调这个过程是几方自愿参与的、有 facilitator 在中间监督的安全的过程,所以我不是“完全不同意”。
不过,修复性正义出发的根基是:犯罪不仅仅是违反法律,也是对受害者和社群造成了伤害,ta 有义务去修补损伤,我蛮认同这个思路的(箱子也是)。
在这部戏里,台词提到,男方在性侵之后还和泰莎调情,并不认为自己强奸了泰莎,之后更是说服了很多人为他写信,说泰莎恶意构陷他,把自己变成了受害者。我认为男方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只是坐牢,也是需要泰莎和他面对面质询,告诉他你就是强奸了,你对我产生了伤害。出于对法律惩罚后果的害怕,男方拒绝承认这一点,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是因为法律眼里只有受害者是正义的,而这也或许是泰莎选择报案的原因——因为男方出于对惩罚后果的害怕,会否认强奸的发生,甚至会试图“煤气灯”泰莎,而泰莎非常需要来自某个系统的证明,证明事件曾经发生。
法律是主持正义的地方吗?
泰莎事发后选择报案,之后痛陈自己失去了什么的时候说“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仰”,所以她仍然认为司法系统是主持正义的地方。当然,考虑到剧情设定上她是一个法律从业者,后续的主题也是“因为我是律师所以我来告诉你,咱们的系统有问题”,有这种世界观并不意外。但是,剥去文本的考量,我会认为,现实生活里,法律很多时候被使用的方式并不是替受害者“主持正义”(当然有一些“补偿性正义”原则的法律可能会更注重这个?但我是门外汉),而是惩罚违反规则的人,但是规则很多时候不等于正义,这个惩罚的权力就会显得有些,怎么说呢,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突然中国语本当下脚了大家大概理解一下,比比划划)所以从根源我就有点不认同。
我不认同法律系统的判决结果就一定代表正义和真相,我也不认为法律系统是人可以找到正义的地方。
也是不巧,我在看《初步举证》同一天的下午,在工作摸鱼的闲余里,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 The Vilification of Megan Thee Stallion。
视频的创作者是一名在纽约职业的黑人女性刑辩律师,也是一个旗帜鲜明废除主义者(abolitionist),主张全面反思当前的刑事司法系统和惩罚系统(the criminal system)。
感谢箱子给了相关概念在犯罪学上更准确的解释:废除主义者,现在基本上是指“监狱废除主义者”或者“警察废除主义者”,主张反对 criminal system,也就是反对当前整个刑事司法系统,包括刑法,定罪,惩罚的逻辑。废除主义是当前北美犯罪学的主导思潮,具体行为包括反对新增监狱,监狱经济制度,落地和社区合作对抗联邦政府新建监狱等等,他们认为监狱原本的四大职能里的 reformation(改造,转变罪犯的犯罪思想), deterrence(威慑,防止再犯),retribution(替受害者主持公道?我乱翻的但大概这个意思)这些东西,监狱其实是做不到的。“当前的惩罚系统仍然是一个 label system,就是你一旦进去了你一生都有一个‘罪犯’的标签,然后按照福柯说的,你就进麻风村了。”
箱子还提到,黑人社区的犯罪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前犯罪学理论的基础。黑人社群是怎么变成贫民窟和所谓犯罪的摇篮的,就是因为在各种各样的结构性歧视和经济不平等之下,犯罪成为了一种出路,而不是罪犯本身就是无可救药的坏人。因为街头犯罪的三教九流不在乎你是不是黑人,但正规职业在乎。然后你进去坐牢了,贴上罪犯的标签,进一步被排斥,被刻板印象,找不到工作,只能继续犯罪,然后二进宫,三进宫,长此以往,恶性循环。
回到视频。Olay 从 Megan Thee Stallion 的案件切入,讨论了惩罚性正义的法律系统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枷锁,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了信念的诠释。我觉得她作为专业人士比我讲的更清楚,有条件的可以看原视频,不过视频原文是英文,我把部分内容放在这里解释给大家。
她认为,责问和惩罚罪犯,并不能解决罪犯的问题。想要解决犯罪的问题,需要的是能预防犯罪,这需要人们去拷问导致犯罪发生的根源问题,之后再去从根源着手解决问题。大规模的监禁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反而会让问题更加严重(因为系统设计如此)。但是,人们习惯于把判决的结果和监禁的结论当作所有问题的答案,并认为其等同于正义。人们不拷问法律,只把司法结果当作唯一的事实标准。甚至很多时候,正因为有惩罚性法律的威胁存在,人们无法要求让其他人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也无法展开坦诚的、治愈的、非惩罚性的讨论和并让施害人改正其行为,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进行修补。惩罚性的司法阻挠人们获得正义。
Megan Thee Stallion 的例子:
4 年前,黑人女饶舌歌手 Megan Thee Stallion 在车外被射击。警察随后赶到,因为 Megan 知道美国警方擅长激化矛盾而非 de-escalate 甚至只要感到了威胁就会直接杀人,所以没有告诉警方同车的黑人男性饶舌歌手 Tory Lanez 有枪,并在脚部中弹的情况下允许警方把她当作罪犯铐起来。
网上相关视频流出,互联网默认是 Tory Lanez 开的枪,并拿这件事取乐,疯狂制作和传播了相关内容的表情包。Tory 找到 Megan 和事件涉及的其他人员私下进行了道歉。
虽然 Megan 没有表达出任何要发声和起诉的迹象,一直保持着沉默,但 Tory 的团队由于知道这类案件是公诉并非受害人起诉,是区域检察院决定是否起诉的。因此为了先发制人,发布了大量混淆视听的消息。
Megan 被激怒,站出来作为证人,与司法检查机关合作,向公众陈述了自己被 Tory Lanez 射击的事实。
Tory 方开始疯狂抹黑攻击 Megan,因为他认为只要能够在公众意见里让这些人不相信 Megan 的证词,他就能获得自由,不用坐牢。因为社会共有的厌女症,Megan 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流言攻击。同时他的支持者也造势,说审判结果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最后的庭审里,呈堂了许多证言和物证作为综合证据,最后 Tory Lanez 被判处十年有期的监禁。这时对他的支持声浪才渐渐退潮。
在这个案件里,最开始 Tory 私下找 Megan 和案件涉及的多方人士都给了道歉,实际上未必没有悔过的意思。问题是在后续流程里;Megan 最开始愿意保护他,也一直沉默,是因为她理解美国的司法系统对黑人固有的种族偏见,所以她并不愿意主动出来起诉,因为她愿意给冲动犯错的人补正修复的机会。但因为惩罚性的司法制度在这里,即使受害者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找到正义,想要给他不用坐牢自我修正的机会,他还是违反了社会的规定,也因此受到惩罚,而他因为害怕和自保,只能选择否定事情发生过,并且抹黑 Megan 是个骗子。
但另一方面,Megan 之所以在最开始没有合作,但是在被抹黑后选择了起诉,也是因为,人们只把法律当作评判正义的唯一标准。人们认为 Megan 在被射击后不主动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和合作,就一定代表了她在撒谎,这件事没有发生。所以她在第一次被 Tory Lanez 团队抹黑后,没有办法坐视自己的公众形象被这样污蔑(她毕竟还是艺人,要吃这口饭),而她凭什么要忍受自己真实经历过的痛苦和恐惧和担心就这样因为“没有和权威机构合作”就被抹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没有别的选择。
箱子补充,Megan 对 Tory 的保护就有一层种族问题在里面,Tory 对 Megan 的反驳有一层性别问题在里面,Megan 的经历就是性别和种族之间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Olay 也因此总结,在现有的体系下,每一个在涉及到性与性别相关的暴力的案件里(暴力,性侵,etc.)受害方要么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料,要么被塑造成故事里的恶人。因为公众会把受害者是否严格的进行了符合法律倡导的行为当作一个标尺,去拿系统这颗石头去敲受害者这枚鸡蛋。
“我不感到绝望,只感到悲伤。”因为在这个过程里,没有人得到正义。
Olay(视频的创作者)同样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她作为一名废除主义者,时常被人攻击说是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犯罪所以才会有这种“白莲花”的主张,所以她有时候会需要提起这件事来自证,并且证明为什么她不觉得司法系统能够给人正义。这件事对她来说只是偶尔会提起的经历,“我从不说我是个家暴受害者或者是个家暴幸存者,因为如果我这样说,人们就会假设这是我人格的全部。但这些假设不是我的真实,我是在遭受家暴后成为刑辩律师的,我也对那些有家暴嫌疑的人没有任何特殊的愤恨。”
我对于讲述别人的创伤性的经历有一些迟疑,在此不详细转述和翻译了,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原视频。
大意是她 20 岁,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友。这名男友因为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有一些过去的经历和创伤。而她不幸成为了一次创伤爆发的出口,承受了来自男友的暴力。她在说服警察不要逮捕男友后,经历了家暴,被男友掐脖子、揪着头发被甩过屋子、被踹头踹出脑震荡,但仍然不愿意男友再次被逮捕。
男友因为家暴被逮捕后给她打电话,说后悔伤害她,而且对自己失望,因为作为一名黑人男性他这辈子最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是进监狱。Olay 理解这里的种族创伤,没有配合司法流程,甚至在周围社交圈纷纷谴责男友的时候,努力替男友保留他的社会网。她替男友写了一封 leniency letter,向法官和法庭解释她的男友有精神上的问题,需要心理健康方面的治疗而非监禁。男方的朋友和母亲都说这封信因为承认了男方做错了事情有发生,对男方不利,是恶意的。
Olay 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在不否定我经历的基础上支持他。”
因为她的不配合,最后检方没能给男友立案。而在男方出狱后,两人周围的社会网反而驱逐了 Olay。那些第一现场见过 Olay 刚刚被打完样子的人,开始否定 Olay 的经历,并且开始贬低 Olay; 而那些陪 Olay 去做验伤检查,在医生诊断她有脑震荡的时候也在场的朋友,也开始说他们不相信男方真的攻击了 Olay。因为他们只接纳一个没有犯过错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社交圈;因为法律的真相只有一个,“证据不足”,所以必然是 Olay 撒了谎。
一方面,Olay 作为一个废除主义者,可以理解那些在性别相关犯罪上想要把人全关起来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如果没有这道判决,所有人都会出来否定她们遭受的伤害和经历。另一方面,也因为生活中没有除了法律之外的坐标,没有社群的共识和规则,所以前男友害怕坐牢,害怕成为被社会额外驱逐的人,为了自保,只能否定他人经历的经验。
她认为,应当在法律之外,在社群之内,建立一套可以承认事实,让人承担责任并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做出弥补的机制。如果社群(community)和社会共识里,没有其他的方式能让犯错的人承担责任,而只是疯狂替此人开脱、洗白、否定行为本身存在的话,那么废除主义是推不动的,也不该这样去做废除主义。
而我额外一层附加的感受是:法律也不应当是事实的唯一标准——法律的真相,只是法律的真相。
小声 BB
最后随便叨叨两句。
其实这部戏还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太,怎么说呢,网红话语叫“高配得感”,英文叫 entitled 了。因为女主的文本逻辑某一部分提炼出来就是“我感情受伤了!系统不够考虑我!系统错了!”让人忍不住感觉十分呃呃。因为如果你认为系统的目的是保证每个人都获得公平和正义,那这里面未必包括不让证人的情感受伤害……
和箱子聊的时候箱子也觉得这个戏做二元对立其实就是默认对立白女白男。“很难想象如果这个陪审团里出几个亚裔黑人中东人 gay 铁 T drag queen 会有多热闹,这样的话女主绝对不会说‘四个女人,我不知道’,因为以上这些人反正也都受够白男了,这些人上来白人就要倒霉了。” 我狂笑。“白人嘛,头顶上除了系统一无所有,因为要团结男的,也不会直接攻击说男的不行,所以那就系统错了。系统没错也错了。”
